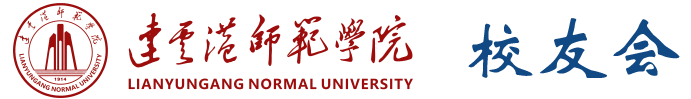在海州师范读书的日子已是32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正是共和国最饥饿的年代。然而学生们在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带领下,努力学习,积极进步,始终以饱满的情绪克服困难。那一段火热的学生生活,一直很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1959年8月底的一天,海师的二、三年级同学,用平板车拉着我们的行李,把我们从海州火车站接到学校。那时海师的大门朝南,大门口挂着欢迎新同学的横幅标语,宽大的校门两旁。蹲着两尊巨大的石狮,气宇轩昂。一进校门,宽阔的黄沙路直通内院,路两边是一簇簇一人多高的冬青树球,身后是整齐苍翠的松障。校园内房舍整齐,树木参天,宽阔的操场,齐全的活动器材,还有地理园、音乐室。路边、墙上、板报栏内,不时看到提醒同学们勤学习、懂礼貌、讲卫生、说普通话之类的标牌。教室里,不时传出书声、琴声、歌声……,这一切,对于一个从农村来的青年,无疑是换了一个新的天地。处身于这个环境,我的感觉是:这里真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。
开学典礼上,老校长桑淑尊给我们作形势报告,进行专业思想教育。讲台桌的绿色台布上,绣着“讲真理、育英才、为师之乐业”几个红字。这是往届毕业生送给母校的纪念品。不知是谁的这句名言,使我蓦然领悟到教师的伟大,所以至今没有忘记。
那段时期,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,但也是活泼紧张和愉快的。每天清晨,即使是寒冷的冬季,天还没亮就被起床号声叫醒,大家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,洗漱完毕,到操场上跑步。经常是起床的号声刚停,就听到桑校长招呼学生起床的话语声。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跑步,晨练以后是早自习,然后才是早饭。
当时每学期每个年级一般要开12门功课,不论哪一门,教师都认真地教,学生都认真地学。因为老师们一再强调,目前我们小学教师所教学科,还不可能专职。因此,当一名小学教师,知识必须全面,才能适应小学教育工作的需要。给学生一碗水,必须自己有一桶水。学而知困,教然后知不足。这些话,一直印在学生们的脑子里,只要是能学的东西,能练的本领,同学们都拼命地学,认真地练。每一个体育动作,每一个儿童游戏都一遍遍地做,每一首歌曲都反复弹唱。清晨、傍晚、星期天、节假日,树下、花间、教室里、操场上,同学们背书的、视唱的、练粉笔字的……谁都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。
学生们都住校,早晚自习时间比较充裕,同学们都在安静地看书、作业。大家把眼前的学习与未来的工作联系起来。那时候学习苏联,学习成绩采取5级记分法,3分及格,4分良好,5分优秀。平时测验多为“突然袭击”,每次课堂提问都记分,而且要求学生到讲台上回答问题,一切都是从难、从严要求。每学期,学校都要开展“开门红、日日红、月月红、满堂红”活动。就是要求每个学生开学不迟到,每次测验、课堂提问都得5分。学习成绩登记表贴在教室里,一个月总结一次。同学们勤学苦练,你追我赶,大家用自己辛勤的汗水,争取“满堂红”的成绩。校园里充满了积极向上、勤奋刻苦的学习气氛。
老师们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和敬业精神,令人敬佩。各学科教师都有各自的教学特点,而严谨、认真、负责的精神,渊博的知识,生动的教学是共同的。
师二年级以后,教我们语文的是王焕民老师。他平时说话不多,很少笑容,表情似乎只是一个模式。但讲起课来,旁征博引,语言生动,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。记得在教学《殽之战》一课时,他对教材上的一些注释,颇有不同意见,就把自己的一些见解写成文章,要我替他誊清。后来他的这篇文章,发表在一家教育刊物上。他还常常把我们叫去,拿出我们的作文,一一当面指点。有时他把改过的地方和我们的原作文比较,说出改的道理,也允许我们提出不同意见;有时他只是指出问题,要我们自己修改,然后再给他看。那时我深感这样批改作文,收益大,效果好。后来我在教学中,常常面批学生的作文,多半是受到他的启发。
我们的数学老师是王昭宇,他幽默诙谐,进课堂常常是一块三角板、一把圆规和几支粉笔,有时带书也只是在布置作业时翻翻。圆规和三角板在他手中如同魔术棒,最难理解的几何题经他神秘的指点和引人的提示就能叫你茅塞顿开,而又觉得轻松愉快。有时他故意设下悬念,叫你思考;有时又故意反说,引你辨别。我和几个男同学最喜与他争辩,有时下了课还尾随他边走边争,直到他走进办公室。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。那时我曾默默地想,将来如能做一名数学教师,就要象他那样熟练地把握教材,抓住要点,启发思考,在愉快活泼的气氛中教会学生。
那段时期我们的生活是够艰苦的了。1960年后,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困难,学生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艰苦。一个月的伙食费八元多钱,有时一顿饭只有一碗清水煮地瓜干。白面馒头要隔几天才能吃到一次。常常是玉米面、高粱面或地瓜干面做成的长方形的糕,同学们风趣地称它们是“黄海肥皂”、“锦屏肥皂”、“耐火砖”。中午每人一块米饭,里面有一半是海英菜种子。一个月能吃到一两次肉,尽管只有很少的一点。深冬季节,师生们一起出动,到农村拾菜皮,拾胡萝卜、海英菜种子,以贴补伙食。
每到夏秋农忙的时候,我们都要到农村帮生产队干活,常去的是当时的新坝公社大井、小荡、沙杭等几个生产队,离学校三十多里远。来回都是步行,还背着行李或拉着平车。每天和社员一起干活,既累又饿,有时就拾起撒在路上的黄豆粒、绿豆粒吃,当时觉得很香。记得一天下午,我和王寿全同学被派到三、四里外的一个生产队去抬化肥,回来后,同学们已经吃过晚饭,他们知道我们食量大,特意为我们留了一大面盆煮地瓜叶,回来后拌上盐水,我们毫不费力地就吃掉了。
为了改善师生的生活,校园里凡能开垦种菜的地方都挖起来了。东操场变成了大菜园。在校园的北墙根,盖起了一长排猪圈。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,种菜、喂猪、养羊。
除了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,还要劳动建校。现在学校东操场那条250米长的环形跑道,就是我们那时修筑起来的。1960年夏天,我们硬是用自己的肩膀,从海州东门外的大成窑场抬来砖头,用平车从刘顶拉来石头,盖起了学校第一幢两层教学楼。现在每次来母校,总要到这幢楼上,走进当年自己的教室看看,心里有说不出的亲切感。
虽然那时候同学们生活苦、条件差、学习紧、劳动重,但同学们精神饱满,情绪乐观。是什么原因呢?我常想,一方面是领导和老师以身作则,并且经常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形势和思想教育,日常的教育教学,紧密地与现实、与学生的思想、品德结合起来,并且坚持不懈,持之以恒。再就是艰苦的生活锻炼人,培养人,使人知道珍惜生活。另一条就是在学生中经常进行谈心活动,交流思想,互相帮助,及时疏导解决一些思想问题。所以同学之间真诚团结,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朝气。这一切对世界观正在形成的青年学生来说,无疑是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。
毕业前,学校征求每个同学的毕业分配意见,几乎每个人都表示:“服从分配,到最艰苦、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同学们说到做到,1962年7月的一天,我们这一届5个班200多名毕业生,分别登上开赴赣榆县、东海县和市郊的卡车,在高昂的《毕业歌》声中,挥泪相别,满怀信心地走向新的生活。
32年过去了,海师生活的一幕幕,还像在昨天。三年学生生活虽然短暂,但对我们的锻炼、成长及日后的工作和生活,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愿母校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,愿母校的事业兴旺发达,愿母校的老师身体健康,工作顺利,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。(六二届校友 张义驔)